独算余食廪米。
“廪米”这是廪生所得的俸米。
九十一石五斗当出贡。
一石是十斗。他说每个月领俸禄,你自己记住,等你领米领到“九十一石五斗”你就“出贡”了,就升级了,你就从廪生升到贡生了。升到贡生,廪米就不给了,廪生的缺就让别人来补,这有一定的名额。
及食米七十余石。屠宗师即批准补贡。
屠宗师就是当时的提学,相当于现代的教育厅长,他看袁先生的学问、品德还不错,建议要提拔他。“出贡”就是批准了补贡,从廪生就补贡生的缺了,也就是升级了。
余窃疑之。
他这下怀疑了,孔先生这一着没算对。
后果为署印杨公所驳,直至丁卯年。殷秋溟宗师见余场中备卷叹曰。五策即五篇奏议也。岂可使博洽淹贯之儒。老于窗下乎。逐依县申文准贡。连前食米计之。实九十一石五斗也。
俸禄领到七十多石的时候,屠先生就批准他补贡了。可能屠先生批准之后,也许就升官高迁,也许是调职了。“署印”是代理。教育厅长大概被调走了,现在有个代理教育厅长。这一位代理教育厅长不同意,把他驳回去,不准他补贡,他还继续去当秀才—廪生“廪生、贡生都是秀才”。一直到了丁卯年殷秋溟宗师当提学。他看到“场中备卷”。这些考卷就是落第的,没有考取的卷子还保存着。有些时候,主管的官员会把这些没有考取的卷子拿来,重新看一看,希望发现遗漏的人才。如果真正是人才,他们还是要提拔的,怕的是一时差错遗漏了。
殷秋溟就看到袁了凡的考试卷。“五篇”就是“五策”,即是我们今天所讲的论文,五篇论文。殷先生看了非常满意,非常赞叹。他说这五篇论文,就像是五篇奏议。“奏议”是臣子对皇帝的建议,国家施政应兴应革,他们都可以提出意见,贡献给朝廷,由朝廷来取舍。殷先生说这五篇确实就是奏议。可见袁先生见识很高文章写的很好。而一般对国家兴革提出建议,都是属于大臣的事情,不是小小的秀才做得到的。就是我们现在所谓的政务委员,国策顾问,是他们提出的这些文章。而袁了凡的文章居然可与他们相提并论,可见他的确是有学问。
“岂可使博洽淹贯之儒,老于窗下乎”?“博”是指他见识广博,“洽”是他的说理非常清晰通达,“淹”是透彻,“贯”是文章无论理路,无论是章法结构,都有条不紊。能得此四个字的评语,定是上乘文章,无论是在思想理论,文字的结构,都属于上等的。所以不能叫他终老于窗下,一生只做个秀才,可惜了,应当要把他选出来替国家服务。“逐依县申文准贡”。就是交待当地的县政府,要把这个人提拔起来。“连前食米之,实九十一石五斗也”。
从此处来看,屠宗师是很了不起的人,看到袁先生的卷子马上就想提拔他。可是代理人杨先生把他驳回去了,这就是两个人的看法不一样。袁了凡是有才干,可是从这里我们得到一个很大的启示,那就是有才还要有命,所以人的一生命运主宰了一切。 命、时、因缘都有定数。在里面讲才、命、时。袁先生一定要遇到殷秋溟,他的因缘才成熟。这些我们都应当要明白的。
余因此益信进退有命。迟速有时。澹然无求唉。
从此以后,袁先生真的觉悟,真的明白了。一个人一生的际遇,吉凶祸福,贫富贵贱都有命,都有时节因缘,不能强求的。命里面没有,怎么动脑筋也求不到。命里面有的,什么念头不想,到时候自然来了。他明白了,从此以后无求、无得、、无失,心地真正平静下来了。所以我读《了凡四训》,学佛以后,我们可以称袁了凡在这一阶段,是一个标准的凡夫。我们连一般的凡夫,都不够标准,为什么呢?心不清净,一天到晚还胡思乱想。他的妄念没有了,对于一生的休咎,清清楚楚、明明白白。
所以古德云:“君子乐得为君子,小人冤枉为小人”。为什么呢?因为君子知命,知道“一饮一啄,莫非前定”。小人很冤枉,拼命的追求,不知道这是命里有的。努力拼命求得的,还是命里有的。你说冤枉不冤枉呢?这是指定数,一般人都在定数里。这个时候袁了凡只知道有定数,不知道定数之外还有一个变量,命运是可以改变的。下一段以后就是讲变量,讲立命的理论方法。要按照真正的理论方法去求,就能够改变你的命运。你想求什么就能够得到什么,一切都掌握在自己的手中。佛家所讲的布施。你想得到财富就必须行“财布施”,想得到聪明智慧那就要行“法布施”,想长寿平安,那就要行“无畏布施”,这就是正确的创造命运的方法。按照正确的理论方法去求,都可以得到你所要得的,甚至连成佛也求得到,何况这些世间的小小福报。
贡入燕都。留京一年。终日静坐。不阅文字。
“燕都”就是现在的北京,也就是首都所在地。元、明、清三朝首都都在北京。“留京一年”,他出贡之后就到北京去了,在北京住了一年。“终日静坐,不阅文字”,每天静坐。从这个地方,可以看到他的心地多么清净。心清净了自然就生智慧。一般人智慧不能现前是心不清净。他之所以能够静得下来,就是他对于自己的命运完全知道,想也没用处,所以什么都不想了,心定下来了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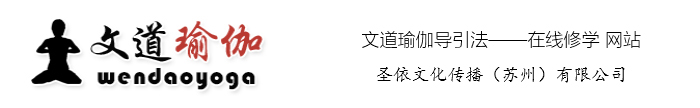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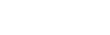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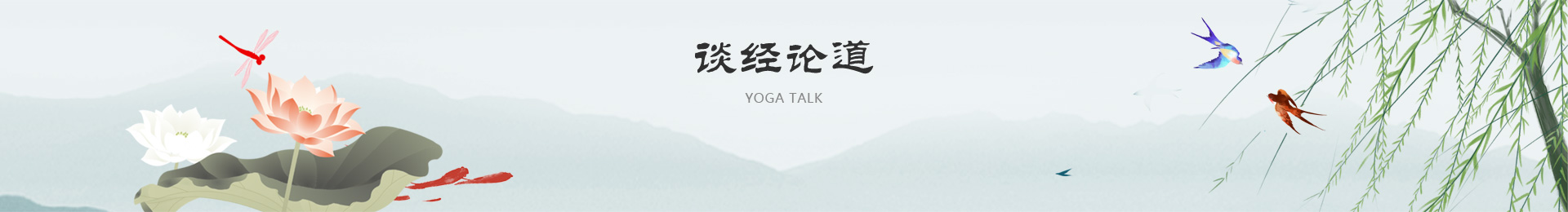
 您现在的位置:
您现在的位置: 



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