余逐起读书之念。
进学念书这个念头就生起来了。
谋之表兄沈称。言郁海谷先生。在沈友夫家开馆。我送汝寄学甚便。余逐礼郁为师。
这是说生起读书进学的念头,往从政的道路作预备工夫。以前读书并不像现在有很多学校。清朝之前都是私塾教学,没有学校。国家只有大学,没有中学。必须私塾里念得很好,才有机会考入大学。那时称太学,明、清都叫国子监。相当于现代的大学,是国家办的。私塾,是私人办的小规模的学校。老师只有一个,学生通常只有二、三十人。
正好他的表兄有一个朋友郁海谷,在沈友夫家里开馆。沈友夫大概是地方上相当富有的一户人家,因为家里很有钱,友几间空房子,用一间作教室,请老师教自己的子弟,亲戚朋友的子弟也可以到这里来上学。郁海谷先生此时正好在沈友夫家里开馆教学。他就拜郁海谷作老师,进学读书。
孔为余起数。
孔先生给他算命。
县考童生当十四名。府考七十一名。提学考第九名。明年赴考。三处名数皆合。
孔先生算他的流年命运,告诉他,你明年去考童生,就是我们一般讲的秀才,要经过好几次的考试。先要经过“县考”,了凡先生应考中第十四名。县上面有府,府上面有省,这是明、清两代的制度。一个府大概管七八个县,主管称为知府,是在县之上,省之下。民国就把府废除了,改成行政专员。“府考”考第七十一名,“提学考”第九名。“提学”就相当于我们现在的省政府教育厅长,,管一个省的教育的。所以地方上考试,考得取,考不取,考第几名,命里都注定 了。所以到第二年去参加考试,果然没有错,都符合。
复为卜终身休咎。言某年考第几名。某年当补廪。某年当贡。贡后某年当选四川一大尹。在任三年半。即宜告归。五十三岁八月十四日丑时。当终于正寝,惜无子。余备录而谨记之。
我们看这段文,不是只看袁了凡先生,而是看自己。哪一天、哪一月、哪一日、哪一个时辰生死都已注定了,怎么死法也注定了,一生全都是命里注定的,你怎么胡思乱想都逃不过定命。这是千真万确的事实,谁都没法子逃过。
因为孔先生给他算得这么灵,所以就请他算终身的命运“终身休咎”就是一生的吉凶。孔先生把他的流年排到死,什么时辰死亡,都为他排定了。历年的考试,能考取多少名,都给他注出来。
“某年当补廪”“廪”是廪生,“贡”是贡生,“补”是补缺。相当于现代所讲的公费学生。虽然是学生,但是领国家的津贴,每个月生活费由公家补贴。每一个县都有一定的名额,必须有缺了,你才能够递补上去。“某年当贡”。贡是贡生。廪生、贡生都是明、清两代依学生的程度而设立的,不是学位,相当于我们现代的中学生、大学生。但是受到国家照顾,由国家发给他生活费用。从前生活费用是发米,而米多的、吃不完的可以卖钱,相当于实物配给。而现代则用货币来代替食物,是方便多了。至于秀才、举人、进士,相当于我们现代的学位,好比是学士、硕士、博士。进士相当于博士,是最高的学位。贡后某一年他去做官了。“四川一大尹”。“大尹”相当于现代的县长。还有二尹、三尹。二尹相当于现代的主任秘书,三尹相当于现代所讲的科长。“在任三年半”。做三年半的县长,你就得要辞职。为什么呢?寿命到了。五十三岁,寿命也不很长。“五十三岁八月十四日丑时”你就寿终正寝,这还是得到一个好死。可惜你命里没有儿子,“惜无子”。了凡先生把这些事情恭恭敬敬的记下来,给自己作一个参考。
自此以后。凡遇考校。其名数先后。皆不出孔公所悬定者。
孔先生的确很高明,算得很灵。往后每次考试。完全跟孔先生算的名次都相符合,一点也没差错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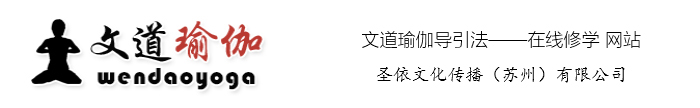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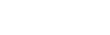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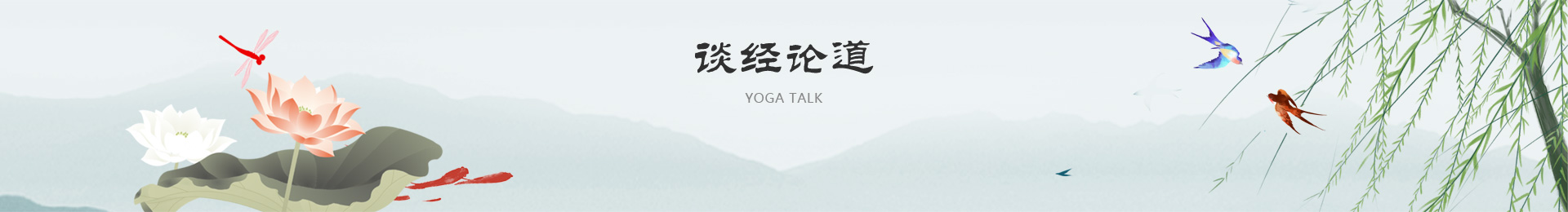
 您现在的位置:
您现在的位置: 




